本文章所属钓区:黑龙江(4066)
(二十二)败走西峪
金栋儿烦了,娘的,这官儿当得不爽!
金栋儿走了。上加工点去了,一个月才回来。
“听人说西峪这阵子上鱼特冲,咱也去趟西峪吧。”十一放两天假,金栋儿又有新提议了。
“西域?呵呵,那一定是张骞开的渔场,不知道怎么收费。”我开玩笑地说。
“什么张骞啊?是西峪水库,平谷县的。”金栋儿对我的孤陋寡闻嗤之以鼻。
“我还以为要走丝绸之路呢,原来就是平谷啊!要去多叫几个人,省得孤单。”
金栋儿联系人去了,反正厂子里爱钓鱼是人有的是。
北郊市场的长途车站人头攒动,上车跟打仗似的。好在我们五个都是正当年的大老爷们,高低没有被老乡的包袱阵挡在车外。金栋儿一马当先就窜上去了,在窗口接我们的提包装备。水库钓鱼需要带很多东西,光鱼食就有十多斤,再加上长 短炮,大包小包,也够累赘的。车上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动弹不得。金栋儿把唯一抢的一个座位让给我了,他自己站在车顶棚有天窗的那个位置,说是车开起来图个凉快。
短炮,大包小包,也够累赘的。车上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动弹不得。金栋儿把唯一抢的一个座位让给我了,他自己站在车顶棚有天窗的那个位置,说是车开起来图个凉快。
两个多小时的行程,颠簸摇晃,终于到了西峪。下车的时候,老唐在一个乘客的屁股底下找到自己的渔具包,老唐傻眼了,新买的两把台湾海竿的竿尖被齐刷刷地压断在塑料包装袋里。金栋儿一把抓住那个坐在上边的人:“眼长屁股沟子里了,赔!”
一车的老乡都没碰我们的钓具,坐坏老唐海竿的那个小子,竟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眼镜书生。那家伙不紧不慢地说:“车上这么挤,我也是被人家推到上面的。不就是竿尖断了么?重新装上还能使。”
“说得好听,那是我刚买的竿子,还没拆封就成残品了,换你你干呀?”老唐也有点压不住火了,“再说了,我大老远跑西峪来是钓鱼的,竿子坏了我还怎么钓?”
“眼镜”仍然是不紧不慢地一笑:“这样吧,我带了四把2米5的海竿,你先拿走玩着,等我把你的竿子修好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草!原来是一路的。
半个多小时的土路,高一脚低一脚,好不容易才转到水边。这又是一个依山的水库,潭深水碧,传说中多有大鱼出没。几个人找好了钓位,接着就排兵布阵。我们几个都是先把海竿打下去,老唐没有动“眼镜”的海竿,而是先支上手竿垂钓。那个书生自然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去修理那两把海竿去了,老唐说,甭管他,这儿就那么一趟车,一条路,他能跑到哪儿?再说了,他的四把竿子比我的竿子贵多了。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没过半个小时就把竿子修完了,表面上看完好如初。我们问他是怎么修的,原来还真是个玩鱼的方家,他说这还不简单,用打火机把竿尖的过线环插口烤热,那截断竿一拔就出来了,然后再把过线环趁热插在竿尖上不就得了。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钓鱼人,抽根烟,赔个笑脸,有什么过节都一笔勾销。
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钓友阿贵刚打第一竿子就把渔轮前端的旋压螺母连同鱼食一块打到水里去了。一把新买的104轮成了废物,还玩个屁呀?水面太大,物件太小,根本就找不到了。我把我的备用渔轮给了阿贵一个,让他将就使着,好在老唐的手竿先上鱼了,钓了一条不大的鲫鱼。金栋儿和阿贵也上鱼了,金栋儿的鱼拉半截跑了,阿贵那条栽了三回桩子,半个多钟头才来上来,是一条一斤多的小鲤鱼。我这儿没什么收获,水底下都是石砬子,我那两把海竿挂了七八次底,光组钩就扔进去四副。我干脆也改手竿了,想打个窝子,把酒米倒进窝子罐里,挂在钩子上就扔到水里去了,那是个触底式窝子罐,等我提竿起来一看,嘿嘿,罐没了,是我自己忘了把牵引绳拴到鱼线上,还有比这更糊涂的吗?
一个罐值不了什么,只是觉得挺别扭的。几个小时过去了,一共才钓了几斤杂鱼。金栋儿今天也不行,坐那儿总犯愣,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头疼。
心里有些郁闷,起来转转,到附近看看别人的钓况。问了几个人也说底脏,没办法玩海竿。那些人都转到东岸浅滩去了,据说那边出鲤鱼,已经有人上了15斤的大鱼。一晃就到了傍晚,要转场也得明天再说了。再往前走,我看到那个压坏老唐鱼竿的眼镜先生,他用海竿,一提鱼护,好家伙,钓了有20多条鲢子!他用的是定点钓浮的方法,鲢子上钩以后也不容易挂底,所以才频频得手。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啊!
我们都没有带酸食,所以也没办法钓鲢子。一直耗到收竿,阿贵又钓了一条三斤的草鱼,其余几乎都是白板。
因为准备夜钓,所以没有去村里找旅馆。为了防备下雨等恶劣天气,我们沿田边找了一间看青的空房,其实那就是个没了门窗的棚子,能抵挡一阵就够用了。稍事打扫,各人铺好自己的“床位”,也就是到房子外面拔些草垫到塑料布下面,软和一点就成。吃了些自带的干粮,都料理停当以后,该张罗夜钓了。金栋儿说他不想去了,留在棚子里给我们看着东西。走不远就是水边,于是我们几个又下竿垂钓。这里的地形还是很难受,不断地挂底,弄得人兴致全无。玩了一个小时我就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玩吧,我回去跟金栋儿就伴去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金栋儿,他的情况太反常了。
金栋儿已经躺下了。
我问:“你怎么了?好像不合适?”
“没什么,头疼。忍忍就好了。”金栋儿说。
我把手搭在他的额头上:“好家伙,你在发烧!”
“路上在坐车的时候吹着了。师傅,我好冷。”
阴天了,下了几滴雨,晚上这地方还真有点冷。我摸出一片扑热息痛,倒了点水,把药放到他是嘴边:“把这个吃了!有病怎么不早说?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有点事还不抓瞎?”
金栋儿说:“没那么邪乎,头疼脑热算不了什么。睡一觉就好了。”
我把雨衣让他穿上,我的雨衣是军队的那种胶布雨衣,很厚实,怎么也能搪寒了。可金栋儿还是冷,我把一叠报纸拿出来帮他穿在衣服里,胸前背后都有。两条腿也裹上报纸,包上塑料袋,金栋儿说,暖和多了。
头12点那几位大侠也回来了,除了身上多了几个包,基本上没什么收获.
(二十三)乘虚而入
一夜无话,不是拍蚊子逮虫子就是起来撒尿。天刚亮阿贵就喊上了:“今天到坝下,据说那里出的是一水儿鲂鱼。”
“有没有咸带鱼呀?靠,反正我不去,我还要睡一会。”金栋儿的情绪仍然不高。
我跟老唐商量,你们先走吧,金栋儿有些发烧,我们俩看情况再说,也许去找你们,也许直接就回去了。
最后我和金栋儿还是选择了打道回府。
回去的车比来的时候好坐,每个人都有座位还坐不满。我和金栋儿半躺半坐占了车最后的那一排座位,身边是已经轻了很多的行囊,脚下是头天钓的那几斤杂鱼。也许我的还要多一点。说不上来心里的不痛快,每次出行钓不到鱼空竿的时候也有,但从没有这么失落的感觉。
“金栋儿,好些了吗?”我问。
“早就不发烧了。”金栋儿说。
“听说车间分了你一间楼房,你小子还挺有福,师傅我都没有房子。”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我相信除了我,别人恐怕不能这样直接切入。
“车间为了让我安心在加工点常住,所以才报请厂子分了我一间过渡房。这样那娘俩过日子就不遭罪了。”
“家里,都安排好了吗?”我特意把家里两个字说得重了一点。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但却永远像一个贪玩长不大的孩子。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搬家,都安排好了,明天就得回加工点了。”金栋儿说。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跟师傅说一声,也许能帮得上忙。”——到底是因为师徒的关系吧,话说到这里我只能这样客气一番。
“不用了,”金栋儿说,“主任说了,家里有什么事车间都包了,领工资,买煤、换气,只要言语一声就成。”
“哈哈,三包!”
“师傅别说了……”
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金栋儿的脸上多云间阴。
金栋儿又去加工点了,一去就是半年。因为不在一起钓鱼,金栋儿便渐渐淡出我的记忆,好像金栋儿这个人物只与钓鱼有关。至于厂里那些好嚼舌头的人们私下里风言风语地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这个木纳的人来说,全都不入法眼也不入佛心。
我写金栋儿钓鱼的故事,已经写了二十三集。提起金栋儿,他也和每个钓鱼人一样,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再长的故事也要有个结局,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文章的结尾早就在我的心里了,我却迟迟不能成文。因为写到这里我才发觉,对于金栋儿这样一个喜剧人物来说,那却不是个喜剧的结局。于是,便有了这段大煞风景的镜头——
据说,金栋儿从加工点回来了,在家里喝了三天闷酒。傍晚下班的时候,他在路上截住了车间主任大人。
金栋儿一句话都没说,抡起16吋的大扳子就向主任头上砸去。主任用手一挡,一家伙竟被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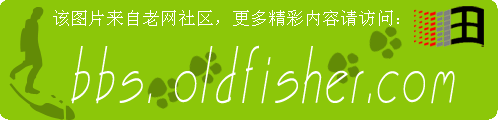 折了胳膊。
折了胳膊。
谁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只知道金栋儿喝了很多酒,他喝醉了,见了我就像孩子一样痛哭。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想,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
钓了那么多年鱼,金栋儿最擅长的就是引逗法,没想到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
——你以为你是钓鱼的人,你钓到了鱼,钓到了房子,还钓到了欢乐。殊不知你也是一条鱼,也许更可悲,你只是鱼钩上那一枚小小的鱼饵。
自从有了那事,金栋儿忽然大彻大悟,好像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十年如磐,只在家守着老婆孩子,再没有看到他在水边钓鱼。
没有金栋儿陪伴,我钓鱼的次数也少了。闲暇的日子,乖乖地在家“相妻教女”,做个模范丈夫。总觉得以前为了钓鱼,亏欠她们太多。我不但要看护幼小的女儿,还要照顾病弱的娇妻。
以前穷困窘迫的日子,仍有许多生活的乐趣,包括旅游,包括钓鱼,我总是兴奋得像小孩子。后来自己有了生意,有了大把的票子,就再也没有时间和闲心到水边踏踏实实地钓一回鱼。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趁老婆孩子入睡以后,才悄悄地把那些封存已久的钓鱼家什打开,把竿子一节一节拔出来,从里屋穿过屋门伸到外屋,然后轻轻地抖一下腕子,想试着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那种让人心动的震撼。良久,妻在朦胧中会呓语般瞩我:睡吧,明天还要去接货呢!
人的命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也许杀生太多,我自己也难逃因果报应。从爱妻病重到病逝,十多年磨难,生死别离,从此心灰意冷,整天灰头土脸地惶惶度日,早忘了还有钓鱼这个爱好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9816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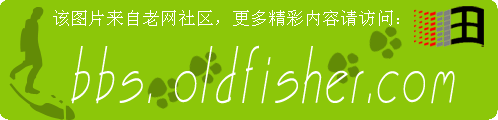 桃木郎于2008-10-22 7:43: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601〖大 中 小〗〖关闭〗
桃木郎于2008-10-22 7:43: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601〖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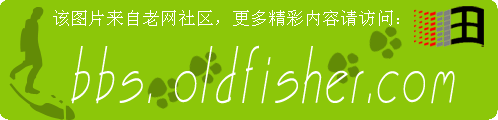 桃木郎于2008-10-22 7:43: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601〖大 中 小〗〖关闭〗
桃木郎于2008-10-22 7:43: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601〖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