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黑龙江(1561) 黑龙江是世界上最长的界河。儿时的黑龙江边,驻有解放军边防哨所,那里有高高的了望塔,塔上装备了高倍望远镜和探照灯。江对岸老毛子(前苏联)那边,也有同样的哨所。漆黑的夜里,双方的探照灯经常扫来扫去,像大海里的灯塔,很远都能看到,让人浮想连翩。 老毛子的飞机,经常在对岸飞,搞侦察活动。我和小伙伴们一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就站在最高的土丘上,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愣愣地眺望着,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为止。 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一年365天,哨所的战士们天天都要巡逻,条件十分艰苦。夏季蚊叮虫咬,冬季死冷寒天,有时要冒着“大烟炮”(暴风雪),趟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巡逻,和电影里描写的一样。那些战士是我和小伙伴心中的偶像,连写作文时都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为祖国站岗放哨。 每逢年节,连队都要慰问解放军,送去肉、蛋和蔬菜等等,当然最多的还是鱼类。到了秋季大马哈鱼洄游的季节,连队都要捕捞一些大马哈鱼分给职工,当然也要特别犒劳一下边防战士。 大马哈属鲑鱼的一种,是冷水鱼,从它们的嘴型和牙齿看,是凶猛的食肉鱼类。大马哈出生在江河里,却生长在大海中。它们历时4年左右的海洋生活,一般要长到60厘米左右,重量在5到7斤,大的能达到10斤。一经发育成熟,就奔波几千公里,于每年的9、10月份,从海洋洄游到出生的江河中,去繁衍后代。由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成鱼在甩完籽之后不久,就会相继死去。腐烂的尸体,则成了出生幼鱼的食物。幼鱼在来年4月冰雪开化的季节,争相顺流而下,它们一路吃着成鱼的腐肉,扑向大海的怀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延续着家族的生命。 为后代而勇于自我牺牲,是很多生物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这种自然规律表现在人类的身上,就升华为血肉相连的亲情,演变成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不知道其它生物之间是否存在感情,但它们为了延续“生命”,而又义无返顾地付出“生命”的壮举,体现着一种尊严,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并予以深刻的反思。 大马哈身上最珍贵的是鱼籽,小时候,父亲把大马哈鱼籽稍微风干一下,用油盐炒香,储在大瓶子里,让我当零食吃。开始还喜欢,后来就吃腻了,但大人们还是哄着,让我多吃点,说有营养。现在,我终于知道它的价值了。 那时没有冰箱,鲜大马哈鱼吃不完,就抹上大粒盐,腌制成咸鱼干保存,有点像湖北老家的腊鱼,能放很长时间。吃的时候蒸一下或煎一下,味道还不错,鱼肉是粉红色、一片一片的,像松木的纹理。 七十年代的河北农村,生活很困难,母亲就把腌制的大马哈鱼干,夹在衣服里,给姥爷、姥姥邮去。姥爷平时不舍得吃,留到过年的时候,就象征性地煎一小盘,端上餐桌。我的那些小表兄弟、姐妹们,欢天喜地一扫而光,如同吃到了最好的东西,很长时间都忘不了。他们终于心服口服地相信我描述的大鱼了。 我们连队面对的这段黑龙江,大马哈鱼的产量不是很高。产量最多的地方在抚远,那里有很多大冷库,后来还建大马哈鱼出口基地。那些年,大马哈鱼特别多,遇到丰收的季节,冷库就把旧的鱼搬出来,把新的鱼放进去。拿出的鱼,来不及处理,很多都腐烂当肥料了,十分可惜。 2004年9月下旬,我在产大马哈的旺季,出差去了抚远一次,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每天江边返航的艘艘渔船,最多的仅收获2、3条大马哈鱼,每市斤要几十元。过去那种“欢声笑语鱼满仓”的景象,很少见了。经询问才知道,我们这边的鱼,都跑到边境线那边去了。原因很简单,老毛子那边人烟稀少,没人捕鱼,生存环境好。也有个别胆大的渔民,冒险过境捕捞,收获确实不小。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来,有些物种是不甘心消亡的,只要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和条件,都会顽强地抗争下去。假如有一天,黑龙江重新变为了祖国的内河,没有了那条分界线,那么,这些可怜的大马哈鱼,还能有藏身的地方吗? (未完,待续)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81637.html 本文章由迎朝阳于2007-11-12 21:46:18最后编辑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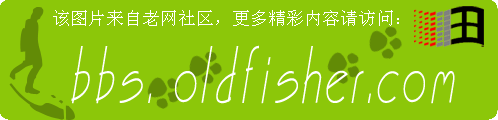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迎朝阳于2007-11-12 20:52: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163〖大 中 小〗〖关闭〗
迎朝阳于2007-11-12 20:52: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163〖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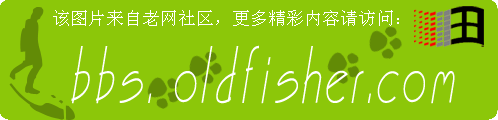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迎朝阳于2007-11-12 20:52: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163〖大 中 小〗〖关闭〗
迎朝阳于2007-11-12 20:52: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163〖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