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吉林(1786) 大风起兮鱼飞扬 东北的深秋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愁的季节。欢喜的是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刚刚结束,金灿灿的大豆和黄橙橙的苞谷成就了农民的钱袋,张家大叔李家大婶 都开始张罗着给儿子娶媳妇给闺女买嫁妆,城里的电器行老板也喜滋滋地数着农民老大哥们送上来的叠叠钞票,人们开始对新的一年充满憧憬。愁的是鬼天气真是个坏,常常是阵阵秋雨夹着瑟瑟的凉风,让出行的人又寒又慄。一场秋雨一场寒,每一场秋雨过后的晴天都不会再有前日的温暖。 那一年的八月节,正赶上国庆放假,吃过早饭后忽然毒瘾大发,在千方百计地否决了老婆提出的“回娘家”议案后,戴上棉帽子,骑上摩托出了门。 呆在屋里还没什么感觉,可一出门就不一样了。那天的风很大,大得行人走路都要竖起领子背过身去。骑着摩托像驾着个小舢板,左摇右晃,冷风打在脸上像被人糊了一块冰淇淋,幸亏我戴了一顶棉帽子并把耳朵系上,才使额头和双耳保持了低温。然而淫风还是从没有设防的袖口侵入,骚扰了我的全身,车到水库,我已经被搞得浑身打颤,再用力也咬不住上、下击鼓的牙。 原地蹦哒了好一阵才稳住了阵脚,体温稍有回升。放眼望去,水面波涛阵阵,浊浪翻滚,好一派北国“风光”--大风吹光了所有的钓鱼人,诺大个水库,只有我老哥一人缩着脖子在寒风中挺挺愚立。当时绝对的想打道回府,但是没有信心,来的时候还有点热乎气堑底,可现在骑摩托回去,非得冻抽!看看大坝虽矮,但蹲下还是能稍背点风,钓,钓,钓!我给自己打气,为了钓鱼死,做鬼也风流! 于是,那一年的仲秋,一个戴棉帽子的家伙,在一个浪涛翻滚的水库,伴着呼啸的寒风,一把鼻涕一把竿,开始了他的“英雄壮举”。 在老家,我们的传统钓法是“扁担钩”。做法是截取约2.5厘米长的旧电褥线,抽出里边的金属丝和石棉丝,在空胶管里穿入尼龙软线,两端各栓一钩,胶管与双钩间露出1厘米软线,铅坠固定于胶管中央。此钩优点是双钩分开,绝无缠绕,鱼儿咬钩时方便无碍;铅坠稍稍离底而双钩着地,漂相清晰平稳而又不迟钝;如遇大风或暗流需要调钝,即使铅坠落底,由于双钩与铅坠间距离较小,鱼儿拉动时上传信息速度很快,漂相依然很好,所以多年来一直不衰,直至今日,传统钓法在那里仍占上风。那天,我用的就是这种钩。 这个水库的鱼情其实并不是很好,钓友们几乎没有在这里获过大丰收。最多的一天下来也不过四、五斤,而且鲫鱼居多。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到这里玩,因为这里还有另一个乐趣,对那时还年轻的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什么东西,这里先不表,以后我另发个文以飨大家。 单说那天决定开钓后,我拿出事先备好的鱼饵(还真是小日本的,什么名怕说出来大家反感,就不说了),又加了点干粉,和得很硬,因为风大用力怕甩钩时掉,用3.6米小竿和9号钩抛了出去,然后龟缩在坝下背风。那天的风拧着劲儿刮,什么沙土粒子、枯树枝子、败树叶子、破草棍子、塑料袋子、空烟盒子……乱飞乱舞,劈哩啪啦直抽眼珠子。浮标在水里随着波浪上起下伏,一会儿峰尖一会儿浪谷,哪里看得清漂相!我心想这下可是栽了,大过节的不在家吃荤菜喝烧酒,跑这里受洋罪,这不是鬼催的吗!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看见浮标放倒了,平躺在水面,不知是风刮的还是流冲的,想提起来看看,一提竿,嗬,有鱼!不知有多大,把我的小鱼竿弯得像半个车圏,大风把竿线吹得山响,似乎有意加大现场效果。我双手合力,使劲儿地拉,一条半斤左右的鲤鱼款款上岸;再抛进去,浮标再次放倒,又一条半斤鲤鱼款款上岸,再抛进去,再次放倒,又……要再描述就是磨唧,恐怕会有朋友砸蛋,不多说。想说的是我这次竟忘了带鱼护!无奈,钓上来的鱼只好直接塞进大背包。 这个水库的大坝很宽,连着乡村公路,时有农民赶着牛、马车经过。见这种天还有钓鱼的,那头裹着纱巾的妇女或手捂着鼻子的男人就议论:这天还有钓鱼的?是疯子吧? 那天钓的鱼都不大,最大的也就是七、八两,浮标的表现方式也只有两种:放倒或黑漂(其它方式也看不出来),但却使我过足了瘾。主要还是大风帮了忙,大风是旁顺风,大风的作用加重了手感的效果,使我手挚半斤小鱼如搏5斤大草,甚是快活。 回家过称,总重三十六斤,成为我在该水库钓鱼最高记录。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65650.html 本文章由真石于2006-12-24 10:10:02最后编辑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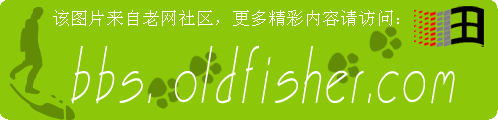 真石于2006-12-22 21:41: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769〖大 中 小〗〖关闭〗
真石于2006-12-22 21:41: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769〖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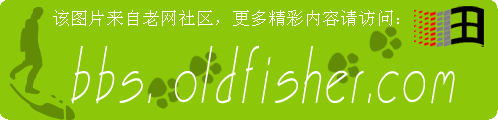 真石于2006-12-22 21:41: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769〖大 中 小〗〖关闭〗
真石于2006-12-22 21:41: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4769〖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