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福建(3862)
我仔细地翻阅《苏东坡年谱》,冀图寻找他曾到过福建的证据。所不幸的是,在苏东坡一生旷久的流放生活中,确实没到过福建。所大幸的是,这并不影响福建人对他的热爱。千年之后,福建龙溪的林语堂先生在海外用英文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传》,不经意间说穿了一个秘密,苏东坡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命运多舛的官员、喜欢月下漫步的诗人,还是一位喜好鱼鲜的厨师和披着蓑衣的钓者。
梁实秋先生曾说,在贴身仆人面前没有拿破仑。因为天生的性情会泄露伟人的秘密。钓鱼真是苏东坡可资探秘的性情人生吗?
水的流向:从眉州到杭州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人。他曾自我评价说,他的文章风格是“行云流水”。确实,这位眉州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水,当然也就不曾离开鱼。眉州是乐山北面四十里的小城,岷江由此汇入长江,县城的边上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被当地人叫做“玻璃江”。嘉佑元年(1056年),21岁的苏轼和他的父亲、弟弟正是从玻璃江出发,过三峡,入河南开封,进入了中国另一个最重要的水系――黄河。嘉佑六年,苏轼解除母丧之制,出任陕西凤翔签判,来到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河流――渭水。这正是中国钓鱼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正源于此。嘉佑七年,陕西大旱,苏东坡前往幡溪姜太公垂钓处祈雨,获应验。在欣喜之余,他建了一座亭子,起名叫做“喜雨亭”,更验证了他与水的密切关系。熙宁四年 (1071年) ,36岁的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激进的经济改革,被外放任杭州通判,开始与江南“相忘于江湖”,他住在西湖边,远处可以望到奔流的钱塘江。他不能与忘情于水,主持西湖疏浚工程,为了避免西湖被荒草侵蚀,苏轼鼓励百姓种菱、养鱼。宋人潘阗以词作《酒泉子》中写到“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在他的人生中,还被贬至广东惠州进入珠江流域,为了到达最终的放逐地海南儋州,他甚至跨越了广西梧州的梧江,乘福建人的大商船,渡过琼州海峡,到达当时被认为是“天涯海角”的海南岛。
水的滋味:从密州到徐州
杭州任期满后,苏轼继续北行,调任密州太守。密州地方偏远,民生凋毙。苏轼远离了朝廷,也远离了一生钟爱的江湖。他仍然渴望水,寻找水,他不由地把他的弟弟苏辙给他的温情当作疗伤的清泉。在密州,他写下了中国人千秋万代传诵的佳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幸运的是,密州只耽搁了他两年的时间,他被改任徐州太守。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苏东坡喜爱此地种类繁多的鱼与螃蟹,因称之为“小住胜地”。
苏轼恋鱼,在他看来鱼在水中的自由和鱼的鲜美一样重要。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指出如果再不治理西湖,任由杂草蔓延,那么水中的鱼儿就面临灭顶之灾。林语堂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佛教的理由,他热爱自然万物,不希望万物因外力而失去自由。他崇尚自由,曾对身边的人说,每条鱼的前身都是人,如果能放生三条鱼,也许在阴间能免去三个受苦的灵魂。在《望湖楼醉书五绝》中,他轻快地写到“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更有令人姹异的是,他所到过的地方,无论南北都有一个共同的风俗,就是逢节日买鱼放生,或许这正是苏东坡魅力所致吧!
他爱鱼,但他更无法割舍鱼的鲜美。他常常眷恋着“长江三鲜”(河豚、鳊鱼、鲥鱼),在《惠崇春江晓景》中,他吟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一次吃罢鲥鱼,他欣然赋诗曰:“芽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在《鳊鱼》篇中,他写到“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颈,贪饵每遭烹。”他甚至用鱼鲜来评论自己的朋友黄庭坚,说他的文章是 “如蝤蛑(即青蟹)、江瑶柱(即干贝),格韵高绝,盘餮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吃鱼的滋味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东坡还更有许多附会的传说,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与好友佛印之间“东坡鱼”的故事了。林语堂先生干脆总结说:“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水的智慧:从湖州到黄州
苏东坡的日子并不象常人揣测得那样惬意,在元丰二年,44岁的苏轼因一桩莫须有的“乌台诗案”遭政治迫害入狱。他的政敌决意杀之而后快,判处司马光、范镇、苏轼、黄庭坚等39人斩首。案件持续了130多天,其中苏轼遭受了严刑拷问。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在等待皇帝最后裁决的日子里,他与儿子苏迈、约定在送饭时加条鱼就是杀头的暗示。一天,苏迈出外借钱,请一位朋友代为送饭,结果不知情的朋友无意中加了一条鱼。苏轼绝望了,写下了给弟弟的一首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传说皇帝看了这首诗后,大受感动最终改判流放黄州(今湖北黄冈市)。
苏东坡又回到了江边,他曾经意气风发地从长江出发,却在魂飞魄散后落回了长江。他经历了丧父、丧母、丧妻、丧子之痛后,带着他的妾和儿子开始过起了农耕的生活。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把钓鱼作为生活的乐趣之一。他写下了《初到黄州》一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个诗人已经开始向一位钓者转型,荒唐的是所谓的政治权力,也许做个“水曹郎”更真实。
在杭州、湖州任通判时,苏轼也曾钓鱼。可那时更多得是钓入山水的浪漫。在《行香子.过七里濑》中,他写到:“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在句里行间,他甚至批评汉代的严子陵隐钓于富春江,是白白浪费了时间,是虚老,是虚名。
黄州并不是浪漫之所,凄苦的生活紧紧困扰着苏轼。他象一个地地道道黄州人那样生活,种地、钓鱼,可是他却感受到了最底层民众对他的真情。他们只是在真诚地帮助一个飘零的钓客,一个不知所终的异乡人。在黄州静谧的钓鱼生活抹去了他曾经的浮华与荣耀,他开始远离斗争、背叛和杀戮,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再来一首《满庭芳》吧!他要离开黄州了,“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山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他希望江南的父老不要忘记他,时时翻晒他穿戴过的渔蓑,或许他还要再回来。
余秋雨先生说:“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水的气质:从惠州到儋州
黄州之后,苏东坡重新走向仕途的顶峰,不幸得是,若干年后再次贬谪广东惠州,继而再贬海南儋州。他曾经的好友与他反目为仇,大加迫害。甚至对苏东坡稍有礼遇的太守全被夺官罢职。可是此时的苏东坡,象一位已经摸清水情的老钓客一般,已是放达自然,处变不惊了。
他在日记中写到,惠州气候甚好,适宜钓鱼,还适宜种植荔枝。他告诉弟弟,他在惠州的江边建了一所房子,可以看到江边三三两两的钓鱼人,可以吃到新鲜的渔获,如果他能来一起吃鱼品荔枝再好不过了。他的放达、乐观与坚忍让政敌们大为光火,重又把他逐出惠州,逼他渡海去海南岛,不给俸禄,不供应粮食。苏东坡又开始重操“黄州旧业”了,这次不同的是,他居然教会了当地黎族百姓种田、捕鱼。苏东坡传授了湖州地区的一种捕捞技术,时称划鱼,所作《划鱼歌》:“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岂知白挺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当捕鱼满载而归时,他开怀地大笑“红酒白鱼暮归,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
钓鱼的气质归根结底就是水的气质。庄子把水看做智慧的源泉,虽然柔若无骨却有千钧之力,可以击穿最坚硬的石头。苏东坡自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钓客之一,他在沉默中坚守着自己的真性情。儋州一位老婆婆看见苏轼落魄的样子,戴着一顶做官的高帽子,裹着一件破袍子,脚上还穿着一双当地人的木屐,问他从京城至此,是否如春梦一场?苏轼大笑,从此之后就把这位老婆婆叫做“春梦婆”。趣闻传到京城,他的政敌怎么也想不通,苏东坡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轻松应对这样的加害。
卑劣必不长久。几年后,轮到他的政敌失意了,流放地正好也是儋州。苏东坡居然提笔给政敌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儋州相比岭南,没有瘴气适宜居住,希望转告他的父亲不必太过担忧。时人愕然,还有怎样如水的气质更值得让人钦佩呢?
苏东坡飘然而去,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钓鱼生活,他也真正把自己看做一个钓者,即使波涛汹涌,我自钓守真性情。在千年之后,另外有人提起了苏东坡“蓑翁”的情怀。当吴仪同志面对SAR疾情时,兼任卫生部长,有人问她怕不怕。吴仪笑着说:“小女子学过苏东坡。”当即朗诵苏词《定风波》一首:“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5734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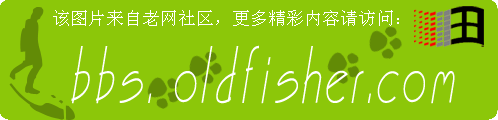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kico于2006-7-21 14:37: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3863〖大 中 小〗〖关闭〗
kico于2006-7-21 14:37: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3863〖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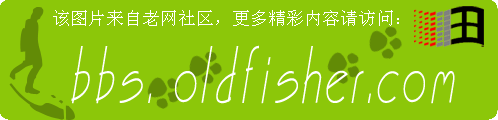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kico于2006-7-21 14:37: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3863〖大 中 小〗〖关闭〗
kico于2006-7-21 14:37:00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3863〖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