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四川(3876)
钓鱼这项活动除了需要技巧和经验,有的时候还需要那么一点运气。问题是,运气并不总是垂青于钟爱钓鱼的人,上帝慈爱的手似乎更喜欢放在那些初学者甚至是旁观者的肩膀上
这天,我的好朋友塔德·哈斯比轻快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吹特吹,说他七岁的儿子布里恩(上个星期天才开始摸鱼竿)钓到一只6磅重的大嘴鲈龟,还将它弄上了岸。
“是从比得湖里钓起来的吗?”(你用一只手都数得完比得湖里的鲈鱼。)
“可不是嘛。”塔德说。
“他本来是想钓鲦鱼的吗?”
“是啊,可……”
“用鲑鱼籽钓?”
塔德只好罢休:“你怎么猜到的?”“我没有猜,”我说,“能够从比得湖钓起那么大—条鲈鱼来的惟一的人,是像布里恩这么大的一个本来不是为了钓鱼的小孩子,而且还必须在一天错误的时辰使用错误的渔具在错误的地点钓。而且,当然,如果他本来不是要去钓鱼,那是很有益处的。”塔德终于靠在我的办公桌上泄了气。“真是离奇的一件事,他本来是想去看足球赛的!”塔德摇头,跌跌撞撞地走出我的办公室,他跟平时一样感到惊异,不知道我从哪里得到这种未卜先知的怪才,编的一个钓鱼故事还没有讲我就知道了。
非常熟悉钓鱼的人经常碰到不同运气。好运气、运气一般、运气不好、运气极坏、倒霉透顶、初学者的运气、老手的运气(我一般属于这一类),当然还有旁观者的运气。塔德的孩子之所以能够钓到这样一条可爱的鲈鱼,道理非常简单:他碰到两种最好的运气,初学者的运气和旁观者的运气。
人人都知道初学者的运气:这种运气持续约一年时间,它使初学者信服,钓鱼是如此容易的一件事,然后,当他或她正要学会如何吹嘘的时候,沙扎啊姆—声!运气跑了,再也不回来。垂钓老手明白这个道理,当初学者钓到一条极难得的鱼种时,他从来都不会抱怨。(他有可能哀叹几声,但你不会听到他抱怨。)
旁观者的运气是一种别的东西。为防读者万一不明白旁观者的运气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讲这个现象。
旁观者通常是闲得没事的看客,吊儿郎当的人,他本人不钓鱼,或者不是特别喜欢钓鱼,但是,事有凑巧,碰到有人非塞给他一根鱼竿,他也就只好拿着一起去,不知怎么着慢慢就涉足随便哪片水中,然后钓起那片水中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条鱼。如果10公顷大的一片水域里一整天都没有一条鱼咬过钩,你基本可以预想到一个旁观者甩一根没有诱饵的鱼线到水里,然后钓起一条鱼,一般来说还是一抛下去就咬了钩。
几乎没有哪位活着的垂钓者能够容忍一名钓到大鱼的旁观者。如果看到旁观者从自己最喜欢的那片水域里钓起一条战利品.垂钓老手的典型反应是一个微笑,说几句恭喜的话,然后悄悄走开,闷头乱走,想寻一块钝一点的石头给自己的脑袋来那么一下。
但有时候,运气特好的旁观者也会碰到最后倒了大霉的时候。“我的老天爷呀!”有个家伙这么大叫一声,那是一天早晨,我们一行五六个经验丰富的垂钓者挤在一处,欣赏他刚刚从斯内克河钓起来的一条重达24磅的母虹鳟。“我这可是第一次钓鱼啊。我本来是个打高尔夫球的人。真没有料到钓虹鳟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一边吼叫,一边用吓死人的口气威胁别人,终于鱼竿赶跑了想滥施私刑的那群暴徒,并护送那名年轻人安全地坐到了他的车内。“听我的话,”我说,“赶快离开这里。那几个人有的两年都没有邂逅一回了。”
“什么叫邂逅?”他睁大天真无邪的眼睛问。
我本人当年都已经到那条河里去过27趟了,一次都没有碰上好运气,因此产生了鲁莽一回的强烈冲动。但是,我很明白旁观者的运气,而且一向都有无可挑剔的自制力,因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对那个年轻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双手卡住他的喉头之前,他已经溜掉了。不过,我还是花时间去看了自己的心理医生,并回头确保自己在那块大石头上的位置———别的人正在将自己的脑袋往上狠撞。
我第一次遇到旁观者运气现象还是自己小的时候,但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件事情的受益人是我哥哥约翰,当时,我与他还保持着温情和相互爱护的兄弟关系———当然你得忽略我不时想生出办法来弄死他的冲动。约翰个子比我高,身体更强壮,比我长得丑,公平打斗时他可以轻易取胜。但他总有出毛病的时候。例如,星期六早晨他宁可去看罗依·罗杰斯的电影也不去河边钓鱼,这使我觉得他是个病得不轻的怪男孩。
“我们去钓鱼吧。”有个天气晴朗的夏日早晨我说。
“不去,我们去看电影吧。”
“妈!”我大叫,“快来量量约翰的体温!”
由于家里的规定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得单独去河边,因此我得想办法让约翰一起去河边钓鱼。敲诈是最好的办法,但那天早晨我手头上并没有掌握极不利于他的罪证,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公然用50美分行贿。因为约翰的原因,我从来都没有存够钱去买自己的自行车,结果成了邻里当中惟一一个踩着弹簧单高跷上中学的男孩。
在爱荷华州的那个早晨,我们带着鱼竿、蚯蚓、苹果和满心的希望沉甸甸地出发了。由于约翰一开始就不想去钓鱼,因此我扛起了所有的负重。到达我们最喜欢的回水地域以后,我们立即就让浮子跳起舞来。
“唉呀呀,”20分钟后,约翰叫唤起来,“这可真是无聊。我们本应该去看电影的。(99%的旁观者都是这样一边往回拉鱼,一边说这类的话的。)我要去下游找山洞和箭头玩。”
我挥挥手让他走,自己专心钓鱼。按照当时的速度,我猜想布恩河这一段的所有鲶鱼将在午饭前被我全部钓完。
半个小时后,约翰沿河岸狂奔而回。“我的老天!”他呼哧呼哧地说。“我刚看到一条鬼鱼。快来!”我们快速冲过去,约翰边跑边将柳条投得呼啦啦的,好让它们抽到我脸上———他干这个一向很在行———然后我们就到了他看见那条大鱼的地方。
“就这儿,”约翰说,他用自己的鱼竿指着一个地方,“我看到它的影子了。”
我们很快将阿尔伯特王子牌蚯蚓罐里最先冒上表面的两条蚯蚓穿上,然后投入激流之中,让它们与水流一起飘动.上面也飘,下面也沉,还在一块巨石下面扔过。什么也没有发生。
约翰甩了三竿,然后就放弃了。他慢慢走到下游的一个沙坝那边去,将虫子甩到浅水里,在沙地上撑起鱼竿,然后趴下躺在沙坝上,只留下我这个真正地道的垂钓者一个人在那里钓那条鬼鱼。
我刚刚专心钓了几分钟就听到约翰呼喊起来,然后看见他朝下猛冲,直奔自己的鱼竿。他拼尽力气猛力向上一拉———在那里慢慢啃他的蚯蚓的那条鲢鱼竟然飞出水面,直奔河岸方向,但只到了离岸边一半的地方。我吃吃大笑,正在想办法编个笑话嘲弄他一番,结果发现他的鱼竿卷起来了。
“上钩了!我逮住它了!”他卷线轴上的手柄开始发出呜呜叫声,然后砰地飞出鱼竿外,一直飞到空中去了。他的鱼线开始朝下游漂去。约翰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将他的鱼竿插在沙地里。“他要将我拖进水里了!”他大喊,“快来帮忙!”
现如今,一个年轻人面前并不是经常会出现如此完美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到底谁当老大的问题的,尤其是这样一个极富嘲讽感,极不自然的方案,人人都必须承认这的确是个好办法,而且这样一个办法简单透顶,竟至于使我其他的一些方案看起来像是小儿科。要成为爸爸最大的孩子,我现在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尽情冷笑就可以了,然后好好编造一个能够解释约翰失踪的极好说法就行了。
另外一方面,我又急需有他在旁边,这样才能够经常来河边钓鱼,这个念头非常诱人,跟几天之后约翰从靠近新奥尔良的某个地方涉水湿淋淋地爬上岸来的情景一样诱人。另外,到底是什么东西将他拖下河岸,我对这个也非常有好奇心。
首先,我们轮流拉,轮流拖,然后,当那场战斗进入持久并且那条鱼即将把他拖入墨西哥湾里去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某种罕见的团队作战状态,不久就使鱼线为我们所控制了。约翰继续在那里骂骂咧咧的,我当时还是个天真的少年,只好在脑子里记住到底哪些话骂起来比较得劲。不久,一条大得出奇的鱼慢慢冒出水面了,滑溜溜的头首先冒出来。
“抓住他的脖子!”约翰大喊。
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但相当困难。(后来我才知道它根本就没有什么脖子。)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终于将那条怪兽拖上岸了,然后,就跟兄弟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两个在几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是一种什么鱼,然后,更重要的是,这条鱼是谁钓起来的。
因为我花很长时间研究过渔业事务,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条离群的大西洋鲑。约翰坚持认为那是某种狗鱼。考虑到我已经救了他毫无价值的生命,我说这条鱼是我钓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你钓起来的。他持不同政见,并且用尼尔森式腋下握颈法使我屈服。我身体发育不良,无法捍卫自己应得的份额,只好同意占有20%了事。
后来,祖父确定那条鱼是白斑狗鱼。“这是多年来这条河里钓上来的最大的一条!我猜这一定使你觉得自己就是我们这家子的渔夫了,是吧,约翰?”我是个性格开朗的孩子,只当是祖父说话有口无心而已,而且这个想法很快就克服了冲溢我全部的生命、令我热血冲头的嫉妒。
但是,我的确还是学会了一些东西。不管怎么样来解释旁观者的这种极好运气,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现象至少跟初学者的运气一样可靠,当然它烦人的程度就严重得多了。我吸取的另外一个教训是,当一个兄长钓到一条足够大的鱼,并且那条鱼即将把他拖入墨西哥湾里去的时候,一个小弟弟应该站得远远的,就让他一个人拿走全部的荣誉好了。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1318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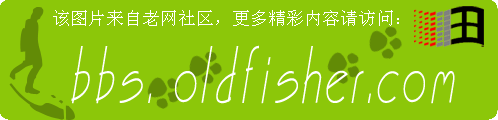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xj于2005-4-22 23:25:00
转摘
发布 阅读指数:3185〖大 中 小〗〖关闭〗
xj于2005-4-22 23:25:00
转摘
发布 阅读指数:3185〖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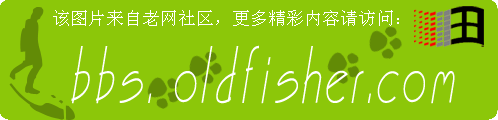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xj于2005-4-22 23:25:00
转摘
发布 阅读指数:3185〖大 中 小〗〖关闭〗
xj于2005-4-22 23:25:00
转摘
发布 阅读指数:3185〖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