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四川(4127)
春节愈来愈近,寒气笼罩一冬的乌木水库,气温照例会在不知不觉间上升那么一、二度。只要气温升上那么一、二度,那些肥敦敦的鲫鱼就会胃口大开,老张从来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眼看年关渐渐地近了,老张急急忙忙地赶完手头的工作,和同事老何约好要美美地钓上一天鱼。老张年纪大了,身子还挺硬朗,四方脸上透着红润,只是受不得风寒,一受风寒就咳嗽不止。忙忙碌碌辛苦一年,老伴实在不愿意老张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再到空旷的野外遭受风霜之苦,给老张布置了一大堆家务活。老张潦潦草草地帮助老伴打扫完家里的卫生,心急火燎地按照老伴的采购清单置办完最后一批年货,已经是腊月二十九。老伴看看实在找不出理由阻止老张钓鱼,在老张的渔具包里塞上两段自己熏制的香肠,一把油炸花生米和一小瓶小土窖酿制的老白干。再三嘱咐早点儿回来。临出门又递给老张一件大衣,老张嫌累赘,推托再三,老伴道:“受了凉,晚上回来又得咳嗽半天。带上!”
冬季钓鱼的人本来就少,眼看过春节,钓鱼的人就更少了。赶到黄家塝的渡船码头,还是只有他和老何两人。登上渡船,和船老板商量送到白果树湾,那里的鲫鱼又多又大。摇船的老板外号“大脑壳”,头大如斗,心胸却颇为狭窄,看他们人少,坐在船上纹丝不动,好说歹说,那家伙只是百般推托,不肯开船。没奈何,只能再等上三、五个人,随渡船到对岸的小坝,然后自己想办法。船到了水面开阔处,远处的山峦、树木都被寒雾笼罩,隐隐约约地看不真切。北风在船篷上呜呜地低号着,又呼啸着掠过湖面。往日清澈的湖水波澜起伏,一浪催动一浪,绵绵不绝。老张急急忙忙地赶路,热的衣襟大开。此刻坐在船舱里,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连连咳嗽,急忙穿上大衣。
从小坝到白果树湾要翻过两道山梁。老何不愿意受那份累,就近在小坝的湖湾里摆开了战场。老张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独自一人气喘吁吁地赶到白果树湾。这里开阔的湖水三面被起伏的山峦环绕,两侧山腿斜斜地伸向湖心,显得分外幽静。凛冽的北风起劲地摇晃着山梁上的树梢,水面却只是微有波澜。湾底一个白墙黑瓦的农家院落半掩在浓密苍翠的白夹竹林里,垭口上有两棵粗大的白果树直指天空,这个湾子就是因树得名。水中长满了细长的金鱼草,水草浓密,相互纠结,成片地铺满了半个湾子。这是鲫鱼最喜欢藏身、觅食的地方,难的是鱼钩难以落到水底。老张先在在两处隐约可见的水草的边缘打下窝料,然后向农家讨来一根竹竿,绑上借来的镰刀,拣水草浓密处齐根割去一片水草,露出一个直径二、三十公分的空洞。在三个新开的草洞里打上精心准备的窝料。一阵忙碌过后,老张坐在小凳上,点上一支烟。
水草边泛起一个小小的气泡,那是鱼儿进窝的信号。老张从来不钓第一条进窝的鱼,要让它放心地进食,给其它鱼儿一个安全进食的榜样。待鱼群抢夺起食物来,哪里还顾得鱼钩的大小,线组的粗细?对那几个新开的草洞,老张要等到足足两个小时才会去看第一眼。不慌不忙地点上第二支烟,悠闲地四处张望。身后,一片浓密的白夹竹林在寒冬里依然绿荫幢幢,摇曳生姿,丝毫不露衰败之相。竹林旁的不远处,一丛枯黄的芦荻顶着一簇簇洁白的花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收回眼光,小气泡三三两两地从窝子里冒上来。扔掉烟头,挂好蚯蚓,轻轻地荡进窝子,缓缓地紧贴水草放下。三粒星漂刚刚停稳,便一粒接着一粒地依次向水底滑落。手腕轻抖,一条三、四两的土鲫鱼飞上岸来,入手微温。不出所料,鱼群在水下抢食,总是身强力壮的大鱼最先得到食物。连续钓上来三条差不多一般大的鲫鱼,紧接着是一条两把重的小鲫鱼。换个位置,又钓上来两条。
老张知道,早上用长竹竿割草的时候惊扰了鱼群,新开的窝子里短时间内不会有鱼。一边钓着鱼,一边抑制着到新开的草洞试探一下的念头。等到看了七、八次表,足足两个小时过去了,才在一个新开的草洞里满怀信心地放下钓组,就等着浮漂在一下轻轻地颤抖后,再静静地滑落,心灵会随着浮漂那一下轻微的颤抖而颤动,那是老张最惬意的时刻。奇怪,浮漂一粒水下,一粒水上,中间一粒半浮半沉,就好似冻结在草洞里,半天没有动静。中午时分,老张已经到新开的草洞里试了无数次,一次比一次的间隔时间短。浮漂依然没有丝毫动静。肚子有些饿了,就着老伴塞在包里的香肠,胡乱啃了几口干粮。摸出花生米,一颗接一颗地将花生扔进嘴里,吃得啧啧有声。摸出装酒的小瓶,嘴对着装满老白干的瓶口,小小地抿上那么一口,一股浓烈的辛辣感觉由舌尖直传到喉头,连胃里都感到一种舒适的暖意。芬芳的酒味由鼻端直冲上头颅,心头的寒意驱除得干干净净。
到了傍晚,陆陆续续钓了约莫有四斤鱼,可是大鲫鱼却没有几条,只有一条在半斤开外。那几个新开的窝子里依然没有一条鱼上钩。冬季鱼儿的活动量大大地减少,受到惊扰的鱼儿短时间不会回到新开的窝子里觅食,原本就在老张的预料之中,奇怪的是整整一天都没有一条鱼。老张看着那一片十分宽阔又背风的水面和水下密集丛生的金鱼草,那是鲫鱼最好的藏身所在。可以肯定的是,那片金鱼草里藏有许多肥大的鲫鱼,问题是没有给它们足够的时间。窝子里喂了那么多香喷喷的饵料,明天一定会上来大鲫鱼。对!早点收竿,明天再来。回到小坝,老何的收获更差,只有两斤左右,个头也更小。位置又当风,冻得早已坚持不住了,远远地看见老张过来,急忙收拾东西。看了老张的收获,老何有些后悔没有跟老张一起到白果树湾。老张趁机提议道:“对,明天我们再去白果树湾,那里好钓鱼的位置太多了,再去几个人都没有问题。而且一点儿风也吹不到,可暖和啦。”老何说:“您疯啦,明天大年三十,谁会来钓鱼?”回程的船上,老张再三用白果树湾的大鲫鱼引诱老何,老何只顾摇头。
晚饭的时候,老张只管想着如何对老伴开口,嘴里喝着辛辣的老白干都没有觉出味儿来,当成解渴的开水往下灌。老伴说:“慢着点儿,又没人和你抢。”吃完饭,老张习惯地要咳嗽两声,刚张开嘴,忽然想到一声咳嗽极有可能被老伴认作是感冒,成为反对自己钓鱼的理由。强忍回去,抢着帮老伴收拾餐桌,又赶着问老伴:“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做?”老伴笑道:“你忙了一年到头,今天又在野外冻了一天,就好好地休息休息,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孩子们都回来了,只管看看电视,等着过年吧。”老张趁机撒谎说有老何做伴,自己明天还要再去钓鱼。老伴瞪大了眼睛,满脸疑惑地伸手摸了摸老张的额头,回手又摸了摸自己的脑门,还以为老张是在发烧说胡话。
第二天一大早,天空零零星星地飘起了小雨。老张没有丝毫犹豫,给老伴留下一张纸条,说自己会尽快赶回家团年,一溜烟地赶到黄家塝,正巧渡船要开了。“大脑壳”问道:“今天您还要钓鱼?”老张说:“是啊,您下午还载客吗?我三点在小坝等您的渡船。”“大脑壳”回道:“下午一点最后一趟。”下了船,通往白果树湾的小路泥泞不堪,一步一滑,闹了老张一身大汗,两腿黄泥。还没有放下手上的东西,就觉得雨点儿飘飘悠悠,似乎下得有些不对劲儿。仔细一看,落在衣袖上的“雨点儿”晶莹发亮,竟然是一簇雪花,下雪了!那雪愈下愈大,雪花飘荡着,摇曳着,自天际绵绵而下,缓缓地飘落在农屋上,撒落在竹林间,消失在湖水里。乌木水库的雪景难得一见,老张却无心欣赏,嘴里连珠价地叫苦。这一下雪,温度大降,只怕自己大年三十要当一回“空军”。
看看昨天新开的窝子,仍然看不出是否有鱼。昨天的窝料下得足够多了,只稍稍补了些窝料下去。钓组是现成的,省去了找底调漂的一应过程。挂好蚯蚓,轻轻荡进窝子,徐徐将线放下。那几粒星漂缓缓向水底滑落,直至踪迹不见。难道记错了深浅?轻提鱼线,握竿的手上分明传来一阵令人心跳的颤抖,那感觉那么令人陶醉,就像夏日里迎面吹来的一阵清爽的凉风,寒冬里灌下的一壶货真价实的五粮液,那种舒坦的感觉从心底里直透上来。那鱼随着老张绷紧的鱼线,摇头摆尾地钻出草间,飞上岸来。是身躯足有巴掌宽的土鲫鱼。再放下钓组,水下的一粒浮漂在稍微停顿后,随着一下轻微的颤抖,缓缓向上浮起,还不等三粒浮漂上升完毕,轻抖手腕,又一条大鲫鱼悠悠地飞上岸来。老张在三个昨日新开的窝子里轮流钓鱼,上来的都是半斤左右的大鲫鱼。乐得老张忘记了寒冷,两手手指尖却冻得发木,僵直得几乎捏不住蚯蚓。鱼钩挂蚯蚓的时候,数次刺的手指出血,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疼痛。一条鲫鱼几乎有三十公分长,老张不敢直接飞上岸,水草间又不能使用抄网,只得小心翼翼地从水草上面慢慢拖到岸边。快到中午,农屋上的黑瓦已经变白,茅草被雪压得低低下垂。看看鱼护里虽然只得二十来条鱼,那重量却在八斤开外。雨帽上微有积雪,身上的雪却随落随化,衣襟、裤腿都已湿透。地上的雪化为泥泞,一步一滑地顺来路回到码头,“大脑壳”的渡船刚到。
一进家门,老伴正在为老张在雪天野地里挨冻坐立不安。看见老张衣襟尽湿,满身泥浆,心疼得了不得。里里外外地忙着为老张拿来白酒暖身子,找来干净衣服,张罗放水洗澡。老张却笑呵呵地拿出那条最大的鲫鱼,向小孙子炫耀,博得儿孙好一阵欢呼。
附图:
夏日的乌木水库
冬季的乌木
乌木的钓鱼人
老张孤零零地一个人
金鱼草
乌木的渡船
老张的鲫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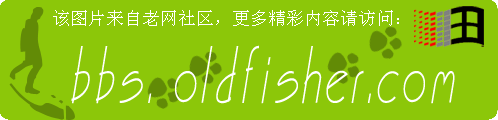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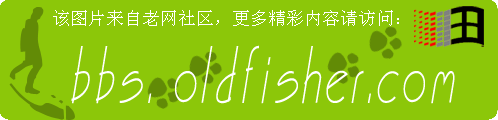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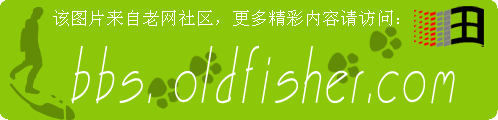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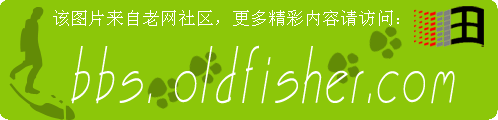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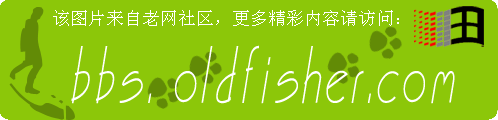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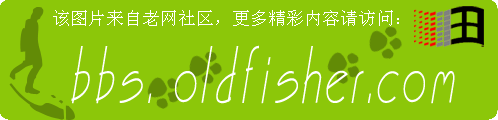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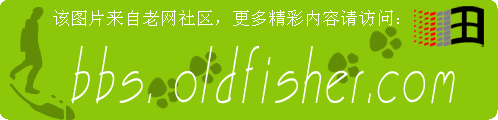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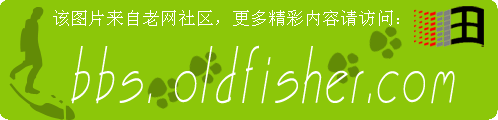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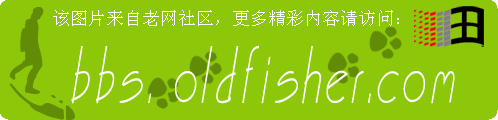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12986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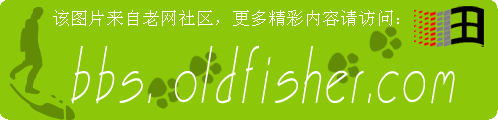 李照成于2014-2-10 10:47:37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889〖大 中 小〗〖关闭〗
李照成于2014-2-10 10:47:37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889〖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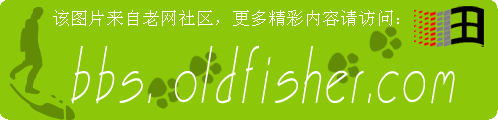 李照成于2014-2-10 10:47:37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889〖大 中 小〗〖关闭〗
李照成于2014-2-10 10:47:37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5889〖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