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河北(2260)
清 明 记 忆
——渔人情感故事
一
又是一年清明至,
春风细雨花草香。
因为一场不得不打的官司,清明前回了趟老家取证。时值清明,迎春花黄桃花红,广袤的田野,小麦绿如墨毯,一望无际。远离城市,湛蓝高远的天空,凌空掠过的飞鸟,民房团簇,杨柳交错,倍感亲切。野风稍凉不觉冷,乡音醇醇褪俗情,置身其中,内心的压抑豁然开朗起来!
取证很顺利。所有证据交给法庭之后,顿感释然。
其实每年清明我都要回老家的,在老家那片散发着草花香气的土地上,祭奠自己故去的长辈。关于清明祭祖,家乡有种说法叫做“早清明”,意思是在清明之前祭祖才是正好。
法庭在集镇的边上,出得法庭走不多远,有家花圈店,从这里,可以买到祭祖用的纸钱。
花圈店的主人是位中年妇女,很瘦弱,一身灰布长褂,戴着洗的发白的蓝色套袖,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埋头认真的扎着纸人纸马。店里光线不好,门口是最亮堂的地方了,屋里地面较外面的马路低了不少,高高的门槛须小心的跨过去才行,人在其中,更象是矮了半截。
纸钱很便宜,无论是黄纸或是纸钱都是一块钱一沓。我掏了十块钱选了其中几种,让那女人用袋子装了。女人话不多,只是用哑哑着嗓子回应着我,言语间,脸上带着窘促的微笑慌慌的帮我收拾着选好的商品。那神情,好象我是突如其来的贵宾或是检查团似得。或许我是她店里第一位顾客,临走时,那女人又叫住我,紧着又从摊位上抽了两沓烧纸塞进我的塑料袋里。我很诧异,这样做买卖的方式我还真是极少经受,习惯了城市里小贩的叫嚣,习惯了嘈杂纷乱的市场,习惯了流莹富丽的商场,而在这低矮的小店铺里,却散发着浓浓的醇朴民风,刻画着一份生意之外的实在。
迈出高高的门槛,外面的太阳显得明亮刺眼。
那女人紧随着出来送我,站在门口,她双手交叠的放在身前,朴素的外表,单薄的身姿,让我内心微微一振,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或许是温暖,或许是亲情,分不情,道不明。在上车的一瞬间,我回头望去,那女人依旧站在门口目送着我。我朝她摆了摆手,她也微笑着也把手举起来,向我轻轻的再见。
她的身影,或许就像灶间做饭的家人?
陡然,她让我想起了去世的母亲。
当兵时探家,我事先没有打电话回去。到家后开开门,母亲正坐在床头专心的织着毛衣。妈妈没有抬头看我,其实,任她再怎么想,也不会想到我会突然从天上掉进这屋里来。
“妈!”我叫了一声。
妈妈看见我,先是一怔,接着兴奋的蹦起来,一把就抱起了我!满眼泪花。
二
烧完纸,顺着田间的小路一路向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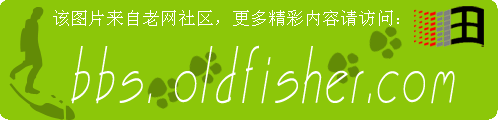 折道返回城里。
折道返回城里。
老家的村南有条河,现在是放水春灌时节,不太宽的河道里,水平静的流淌着。河水下降了许多,河岸两侧,犹湿清新的痕迹记载着流水曾经有过的深度。
这水来自水库。每年,水库总是放水几次,供给下游的千顷良田。等到奔流的河水平静下来,这河就成了钓鱼人的乐园。
午时的太阳暖暖的洒落,河水鳞鳞,波光闪烁。钓鱼人沿河而坐,三三两两稀落的排列着守望着钓竿,凝视着浮标,似乎忘却了时间。
河边的风柔柔的吹着,低垂成行的柳树顺着河道延伸,恰似青玉,把个修长弯延的河道妆扮的格外妩媚。有人把柳条做成了柳笛,单调的笛声响亮的撕破这分宁静,坦率的奏起春的音符。
下得河道,软软的泥土散发着水的气息,泥土乖巧的任由钓鱼人修成平整的钓位,无言的承载着快乐的钓鱼人。浮标扎在清冽的河水里露出红红的漂尾,被起起伏伏的水流拥蹙着,捕捉着鱼讯。
对岸有老两口正在收竿。
这对老人年纪有七荀左右,男的擦拭着沾着水渍泥巴的渔具,女的整理着闲散物品,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他们身后,那河道上面的小路上,停放着一辆小三轮,三轮就像老人手中擦拭一新的竿子,车身上的漆面闪烁着同样的光泽。
收拾好东西的一对老人相互拉着手,踩着松软的河泥向岸上走去,笨拙的身材吸引着人的视线。老爷子走在前面,每一步踩的都是那么踏实,老太太跟在后面,一只手拎着东西,一只手被老伴牵着,顺着老伴的脚印一步步跟上去。
大家的收获都不怎么样,转了几处钓位,钓得到鱼的人不多,就算钓得到的,也是寸把长的小鲫。饵料用的是蚯蚓,因为是活水,无法打窝,加上面饵的作用不明显,大多数人都是把蚯蚓挂在钩上死等。河道北岸向阳,有几位揣着手,把脑袋伏在膝盖上睡上了午觉,看来这河里真正出鱼的黄金季节,应该在停水之后。
停水之后,因水流的静止很多鱼也就留在这河道里安了家。每到此时,总有很多腰间套着充气轮胎的人在河道里电鱼、下粘网,不用几天,连白条都会绝迹,留给钓鱼人的只剩下趴地虎和小麦穗了。河水依旧清冽,而钓鱼人的天空越来越小。那时,小河两岸,只留下丛丛青苇与连绵的树荫为伴,再也见不到钓鱼人的影子了。
… …
渔人的感情是丰富的,身边的故事,点点滴滴,无须笔墨,也无须琴瑟,自是一道风景。而这清明的记忆,伴着沥沥春雨轮回着,随着繁花争荣,万木吐翠,终会走进夏天。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11181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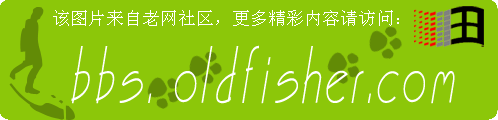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海水于2010-1-9 18:36:56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2873〖大 中 小〗〖关闭〗
海水于2010-1-9 18:36:56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2873〖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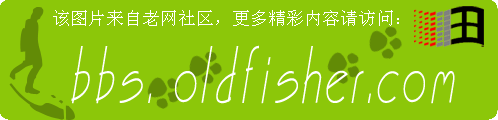 海水于2010-1-9 18:36:56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2873〖大 中 小〗〖关闭〗
海水于2010-1-9 18:36:56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2873〖大 中 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