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辽宁(3355)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重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 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潘 岳(晋)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热的连呼吸都属于力气活。
“秉钢叔,给我做一把木头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不点百无聊赖地拽着他的裤腿嚷嚷着。
只见那人腾出一只大手拎起这个小不点笑呵呵地安抚道:“好,秉钢叔给你做,可得等我和你爸先把手里的活做完。”
那人说完,便转身去专心致志地干活去了,只剩下那个小不点蹲在一大堆木头屑中等待着他一心想要的木头刀。
老爸有三个铁杆哥们,秉钢叔是其中之一。那些年里,他们这伙子人几乎是每个周末都一起出去钓鱼。
秉钢叔钓鱼,手竿的技术是相当厉害的。无论赶上什么鱼情,即使是其他人都空军,他的鱼护里总能多多少少的装着几条鱼回家。鲁叔经常气鼓鼓地埋怨自己的鱼都被他钓走了,而全然不提自己在水边醉了一整天。
而这些记忆都停留在儿时,因为很多原因,秉钢叔十几年前离开了单位,独自一人跑到南方闯荡,自此就再也没了他的音讯。唯一能让我想起他的,就是房间里那张由他和老爸亲手做的双人床,而那把木头刀则早已不知所踪了。
再次见到秉钢叔,已然与记忆中的他完全不同了。消瘦的脸颊,稀疏的白发,深陷的眼窝,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苍老,让人不由得心酸起来。
我赶忙将秉钢叔请进屋里,然后赶忙给父亲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赶忙把话筒递到秉钢叔面前。只见他连忙摇手,并且指着自己的喉咙哑哑的示意着什么。我奇怪起来,他这是怎么了?
一旁的婶子赶忙向我解释:“你叔头年得了喉癌,上个月刚刚做了手术,以后都再也不能说话了。”婶子告诉我:“他一出院就嚷嚷着要来看你爸,说是十多年没见了,也见不了几回了。”
我赶忙转过身告诉电话那头的老爸,让他放下手里的事和老妈赶紧过来,同时揉了揉已是红红的眼圈。
......
“谁看见我的鞋了?”老爸坐在帐篷里问大伙。
大家都不出声,都当没听见似的在钓位上钓着鱼。
“昨晚睡觉时我就脱在帐篷门口了,肯定是你们拿了。”老爸继续问道,可得到的依旧是大伙的沉默。
好在盛夏的清晨不是很凉,老爸无奈地光着脚丫子朝自己的海竿出走去,因为他看到其中一把海竿已经送线了。
狠狠地提了一下竿,然后便是轻轻地往回收线。只见竿梢渐渐弯了下去,果然有东西,老爸已经顾不上光着的双脚,兴奋的摇动着渔轮。
越来越近了,可丝毫没有挣扎的迹象,老爸开始纳闷起来。终于到岸边了,只见铅坠下面的钩上挂着个和鱼全然不同的东西。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老爸正在寻找的那只鞋。
整个岸边终于再也无法沉默了,所有人都爆发出歇斯底里般的笑声。尤其是秉钢叔和鲁叔,笑的连手里的酒瓶都掉在了地上。
“侯哥,这事真不赖我,是钢叉子(秉钢叔外号,因为秉钢叔电焊功夫一流)说你这两天钓太多了,所以才出了这么个馊招。”鲁叔前仰后合地解释着。
老爸咂了咂嘴,满脸无奈的表情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将手里的鞋狠狠地向鲁叔砸了过去。
那是在棋盘山水库的北岸,那年我十二岁。
......
老爸和老妈没过多久就赶过来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当年那个一口气能扛六根方子木从一楼走到六楼的秉钢叔会变成这样,也和我一样瞬间便红起了眼圈。
两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久久都没有分开。
老爸是个憨直木呐的人,从来都不会说什么话,而秉钢叔也只能哇哇的发出些外人听不懂的声音,全靠一旁的婶子当翻译。从婶子的口中,我们知道了秉钢叔得病的经过,知道了这些年他们两口子在外闯荡的辛酸,知道了秉钢叔在南方与婶子去钓鱼时对老爸这帮老伙计的想念......
末了,婶子淡淡地说出了一个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虽然咽喉息肉导致的癌变在发现之后及时做了切除手术,但癌细胞还是扩散到了淋巴。
我不再是那个虎头虎脑的小不点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
大雨从头天半夜就一直没完没了的下着,强劲的风将插在岸边竿子吹的摇来晃去,那场面让人见了就慎得慌。
可这也无法阻止我们钓鱼的热情,老爸他们索性脱去已经湿透了的衣服,直接坐在水里抛竿。
“我们都是神经病!”鲁叔借着酒劲高声哼唱着。
我没心情跟他们一起疯,独自坐在车里观察着不远处的一排海竿。
“秉钢叔...”我摇下车窗朝他们大喊:“你竿子被拽倒了!”
只见秉钢叔哗地一声从水里钻出,扔掉手里的竿子跑了过来。
“哪个?”
“嘿嘿......”
“臭侯儿敢耍我!”
我还没说出来话,就被秉钢叔的大手如同抓小鸡似的从车里拎了出来。
“别别...我衣服都湿了...”我央求着。
可这都没用,一脸坏笑的秉钢叔将我夹在掖下径直走向岸边,不由分说地就把我扔进了浅滩里。
其余的人都哈哈笑着,庆祝我这个小捣蛋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则坐在水里任凭雨水与浪花拍打着,郁闷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眼前那排海竿中的一把静悄悄地就底下头去。于是我赶忙又喊,可大家都坚信我是那个该被大灰狼吃掉的孩子,谁也没理这茬。
那时候的竿子都是沉颠颠的玻璃钢,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才提起那把四米二的大炮,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通收线,竟然拽上来一条四斤多的大鲤。
当我拎着大炮和鱼走过去给他们看的时候,秉钢叔一口认定那条鱼是他的,因为我提起来的是他的大炮。而我则牛里牛气地冲他嚷嚷:拿在谁手里就是谁的。
那是在碧流河,那年我十岁。
......
在我家的那天晚上,秉钢叔和老爸联系了当年那帮老伙计,大伙约定第二天找个酒店聚一下。
据老爸说大家在酒桌上都哭的像个孩子,尤其是鲁叔,那天破天荒的只喝了两瓶啤酒。他说他看着现在的秉钢叔怎么也喝不进去酒,只觉得心难受的要命。老爸还跟我说,秉钢叔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像当年那样和大伙一起去水库钓鱼,虽然身体条件已经很难允许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坚持。他指着桌上的几包鱼钩和线说:这是秉钢叔买的,让我给他绑点钩。我知道老爸的眼神已经很难做这些事了,便二话不说的接下了这个任务。
可秉钢叔并不知道,当年那支钓遍辽宁省大小水库的队伍早已支离破碎了。
袁叔因为开车肇事赔了许多钱,至尽仍在为了还债和养家糊口而奔波着。
宝福叔因为过量吃感冒药被查出了尿毒症,只能在家边擦拭竿子边唉声叹气。
吕伯伯得了腰脱,现在只能勉强走路。
还有两位当年的铁哥们已经去世了。
鲁叔说:“当年那个浩浩荡荡的队伍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些在水边的日子早已成了尘封许久的记忆,而我们则在回忆这些美好日子的过程中衰老着。岁月的蹉跎,就如同那些往事一样,让人回味,更让人心碎.
本文地址:http://bbs.oldfisher.com/show_i111595.html
本文章由houxijin于2010-1-5 21:32:23最后编辑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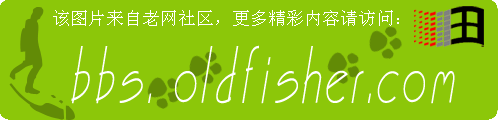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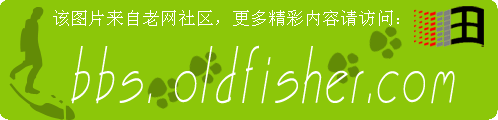 渔村●侯哥于2010-1-5 18:09:29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6554〖大 中 小〗〖关闭〗
渔村●侯哥于2010-1-5 18:09:29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6554〖大 中 小〗〖关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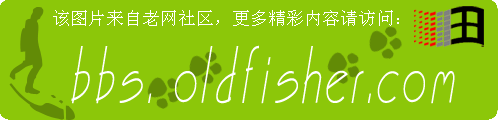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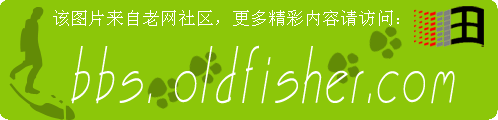 渔村●侯哥于2010-1-5 18:09:29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6554〖大 中 小〗〖关闭〗
渔村●侯哥于2010-1-5 18:09:29
原创
发布 阅读指数:6554〖大 中 小〗〖关闭〗